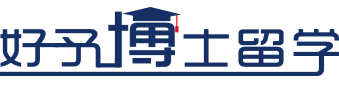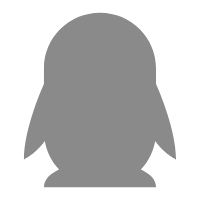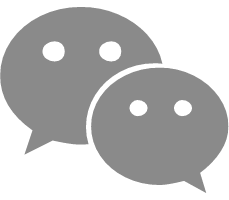医生可以拒绝给日籍华人看病吗?
在网上看到一个争议特别多的话题:
如果一个日本人,或者日籍华人,在中国生病了,医生能不能拒绝给他看病?
光看标题,就够炸的。
在社交平台上,这类问题几乎每次都能引起一场口水战——
有人说:“凭什么?他们以前对我们干了什么你忘了吗?”
也有人说:“医生的职责是救人,不是清算历史。”
那问题来了,现实中,如果真遇到这种情况,医生该怎么做?
我们今天就来好好聊聊这件事。
争议的起点
事情起源于一位医生的提问。
他说,有一次遇到一个从日本回国的华裔病人。
人不算多大年纪,六十来岁,说得一口流利的汉语,但总喜欢夹杂几句日语。
态度客客气气的,可是要求特别多——
要别人排好队、要药品按日本的标准放袋、还不停地说“日本那边多好多好”。
医生心里挺烦:
“你要真是年轻人,我也能理解,可你那一代人……离战争那么近,老了还回来享受咱的资源,还在我面前炫日本?”
他没拒诊,但那种心里的抵触,他忍不住写成了帖子。
结果,一石激起千层浪。
有人拍手叫好,说他有骨气;
也有人直接骂他没医德,说他根本不配当医生。
救人
是职业义务,不是选择题
大多数医生的回答,其实都挺一致的:
不能拒诊。
这不是“圣母”,也不是“和稀泥”,而是职业底线。
因为医生这个职业,一开始就被设计成“无差别对待人类”的角色。
从古希腊的“希波克拉底誓言”到今天的《中国医师宣誓》,
每一条都在强调——
“病人的健康与生命,是医生首要的顾念,不因国籍、宗教、政治或地位不同而有所差别。”
这句话听起来很高大上,但翻译成现实,其实就是:
你穿上白大褂的那一刻,病人就是病人,没别的身份。
哪怕是罪大恶极的杀人犯,在执行死刑前要送医院体检,医生都得按规矩给他看病。
那你说,一个持日本护照的华人,医生凭什么拒诊?
医生的工作
是对抗疾病,不是对抗人
有个医生说得特别好:
“如果医生能因为国籍拒绝病人,那他也能因为贫穷、性别、取向、宗教去拒绝别人。”
今天你讨厌日本人,明天你可能嫌弃穷人,
后天你觉得同性恋让你不舒服——
那请问,你还算医生吗?
医学从来不是立场问题,它是职业伦理的问题。
一个医生最重要的品质,其实不是“医术”,
而是能不能在复杂的情绪里,依然坚持“治病救人”这件事。
有人提到二战时期的例子:
哪怕在抗战最惨烈的时候,中国的医生给日本战俘看病也照样看。
后来建国后,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医务人员,照样给日军战犯诊治、开刀、喂饭。
他们恨吗?当然恨。
可他们更清楚——如果连医生都带着恨去行医,那这个社会的底线就没了。
但现实
也没那么单纯
当然,说到这里你可能会反问:
“那医生就得被动挨骂?病人再无理也不能拒绝吗?”
这也是很多人忽略的部分。
其实,“不能拒诊”不代表“必须宠着对方”。
医生要平等救治所有人,但不意味着要满足病人的一切要求。
有个临床医生就说,他遇到过三类日本或日籍华人病人。
有的特别懂礼貌,语言不通但很客气,治完病还送牛奶表示感谢。
也有那种带点优越感的,讲话夹杂日语,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。
前者让人温暖,后者让人火大。
可不管怎样,医生都得看,但有无理要求,就可以拒绝。
比如想插队、想特殊待遇、想违反规定开药——
对不起,规矩就是规矩。
医生可以拒绝“特权”,但不能拒绝“病人”。
有医生也提到一个细节:
现在医院对“外宾”的接待很谨慎。
因为一旦涉及外籍人士,投诉、外交、媒体都有可能牵扯进来。
所以医生表面看似“不能拒诊”,其实背后是多重的制度和风险约束。
问题的背后
其实是“身份焦虑”
很多人讨论这个问题,其实不是真的关心医德,
而是借机发泄一种“被冒犯的民族情绪”。
我们都知道那段历史的痛,也知道有些人回国后的态度确实让人不爽。
但在医生的语境里,问题不是“你讨不讨厌他”,
而是“你能不能区分人和职业”。
医生不只是一个岗位,它是一种公共服务。
一旦医生开始“凭感觉”行事,那下一个被区别对待的,可能就是我们自己。
有句话说得很扎心:
“如果你觉得医生可以拒绝别人,总有一天,你也可能被别人拒绝。”
今天因为他是日籍华人你拒绝他,
明天因为你没医保、没钱、没关系,别人也能用同样的理由拒绝你。
你愿意吗?
医德
不是天生的,是制度在保护
很多人以为医德是医生的“良心”,
但其实,更重要的是制度让医生不必为良心付出代价。
比如有人举例,以色列的医生在监狱里,救治过哈马斯的头目;
战俘营里的医护照样给敌军看病。
这不是因为他们不记仇,而是因为他们清楚——
医学是超越政治的,是文明的底线。
我们对医生的要求,不该是“完美无缺”,
而是希望他们在制度的保护下,能做出“正确但不吃亏”的选择。
因为一旦制度让医生“有风险”去行善,
那就没人敢善了。
那医生有没有拒绝的权利?
从法律上来说——没有。
中国《执业医师法》第26条写得很清楚:
医生在执业过程中,应当遵守职业道德,不得拒绝对病人施治。
只有在病人违反规章制度、威胁医务安全,或者病情超出本院诊疗能力时,
才可以转诊或中止治疗。
换句话说,你不能因为国籍、身份、政治立场来决定救不救。
但这并不代表医生没有“空间”去处理。
医生可以用专业理由、转诊建议、病情说明等方式避免冲突。
真正成熟的医生,不会让“情绪”影响“决策”。
而且很多时候,他们心里想的其实也很简单:
“别出事、别投诉、别上热搜。”
为什么公众情绪会这么激烈?
其实,说到底,这个问题根本不只是“医生”与“病人”的矛盾。
它戳中了我们更深层的焦虑:
我们对公平的信任,还不够。
很多人觉得社会对外国人太宽容、对本国人太苛刻;
觉得外籍病人能插队、能走特权通道,
所以一听“日籍华人看病”,第一反应就是“凭什么他能先?”
但我们忘了,医疗资源紧张、制度不透明,这才是让人不满的根。
医生拒不拒诊,只是情绪的出口。
真正的问题,是我们希望有一个更公正的系统,
让每个病人——无论国籍——都能被平等对待。
医生的困境
夹在“人性”与“规矩”之间
医生不是圣人,他们也会烦、会怒、会厌恶。
尤其是面对挑衅、傲慢或无理的病人,
任何人都会心生抵触。
但问题是,医生这份职业,要求你得先把这些“人性反应”压下去。
这不容易。
在急诊、在病房、在无数个被骂、被投诉的瞬间,
医生都在练习“克制”。
有人说得很好:
“医生能不能拒绝给日本人看病?
不能。
但医生能不能讨厌他?
当然可以。
只是你得在下班之后再去讨厌。”
这就是职业精神的残酷之处。
我们真正该讨论的
也许我们该从另一个角度想:
当一个医生问出“我能不能拒绝给日籍华人看病”,
其实他不是在问“我能不能仇恨”,
而是在问——
“我能不能有情绪?”
“我能不能有选择?”
“我是不是只能被要求无条件理性?”
社会期待医生是“神”,但医生首先是人。
我们希望他们专业、理智、仁心,
但也该给他们情绪的出口和心理支持。
因为只有当医生被温柔对待,
他们才有余力去温柔别人。
一场关于文明的考题
医生能不能拒绝给日籍华人看病?
答案其实早就写在医学史上了——不能。
但更重要的问题是:
我们有没有为医生提供一个能让他们安心行善的社会环境?
有没有让他们相信——
“选择善良,不会吃亏”?
一个社会的成熟,不是看它多恨敌人,
而是看它能不能在恨里,仍然守住理性和底线。
有医生说:“我治的不是日本人,是一个生病的人。”
这句话听起来普通,却是最难做到的。
因为它意味着,我们把文明放在情绪前面,把原则放在人性上面。
那天你走进医院,你希望遇到的,不是一个爱国战士,
而是一个能救你命的医生。